
 |
|
|||||||
| 論壇說明 |
|
歡迎您來到『史萊姆論壇』 ^___^ 您目前正以訪客的身份瀏覽本論壇,訪客所擁有的權限將受到限制,您可以瀏覽本論壇大部份的版區與文章,但您將無法參與任何討論或是使用私人訊息與其他會員交流。若您希望擁有完整的使用權限,請註冊成為我們的一份子,註冊的程序十分簡單、快速,而且最重要的是--註冊是完全免費的! 請點擊這裡:『註冊成為我們的一份子!』 |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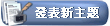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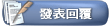 |
|
|
主題工具 | 顯示模式 |
|
|
#1 |
|
長老會員
|
全球華文文學【星雲獎】-人間佛教散文
《入藏》-作者:連明偉 昏沉醒來幾次,很不安穩。眼皮迷茫眨了幾下,辨不得時辰又睡著了。 再次被吵醒,是半夜。司機虎聲吆喝,把車上的人趕下車,吩咐解手。我在車內一盞一盞豆燈下挺身,查看時間,三點半整。夜極深,陰風囂張撲撲撞窗,霧氣泛生。從上鋪往下後,穿越人群。那些擠在走道上的人,難民般,有些蜷縮毯被,有些猛發囈語,有些唉喔幾聲說背真疼,全揉著眼睛不明狀況,拉著陌生的人問,到了嗎?司機口氣差,要我們搖醒身邊的人,說路遠得很,全都得下車,不准貪睡。我小心翼翼踩踏,怕一小心就踩到幾隻手足,傷了人。車燈暗,雙腳或淺或深踏在橘色脫毛的毯被上,近了門,打開上車前發下的塑膠袋,取出鞋套上,下車,伸展身體,終於長吁了一口氣。 每個人都喘大氣,怕吸不到氧,雙手搓著取暖。各尋角落,撒出的尿都帶熱氣,翳進冰冽寒風,又吸進肺,像生命的循環。站著就痛苦,我受不了凍,匆匆脫了鞋放進袋子,上車。鄰座的人早已入位,全身縮進棉毯像冬眠。司機叫喊好幾聲,要人上車後左看右看,人不要多也不要少,多一個少一個都糟糕。車隆隆發響,引擎在寒風中陣陣嘶鳴,車身抖動如初醒的犛牛,富有活力。樂聲轉小。整輛車在暗中行駛,只有駕駛位還亮著火紅的指示燈,像跳動的星。 「遼闊無邊的草原,是我美麗可愛的家鄉,藍天上飄浮著朵朵白雲,恰似草原上頂頂帳篷。一匹烈馬闖蕩天涯,崇山峻嶺中追趕著太陽…」車內的樂聲轉大,光扎雙眼,腰一挺,天亮得唐突。空氣稀薄,卻清新。索性再縮起身,棉毯拉過額頭擋光,卻再也睡不著,只迷糊覷著車的走向。這是第幾天行旅?身在何處?為什麼極力想要拋下過去?或許不必費心考察,日子恍然度過總會留下什麼,而那絕對不是日期。腰桿彎久了,發痠,索性立起椎骨伸懶腰迎日。窗外正是大山大河,壯天壯地,辭彙成了過度累贅。是肅殺,卻又是生機。從臥鋪鐵椅的窄縫拿出背包,掏一袋紅桃,啃了幾口覺得不踏實,又開了包餅乾。水沒喝上幾口,怕路上憋尿,行程又出什麼亂子,霸道的司機大哥不會為了一人的尿意而停車。 這車比想像中實際,或者該稱克難。民營的。從西寧經格爾木,終至拉薩。全程一九二二公里,高度從兩千二突然拔高至五千,再陡降至三千六。途經湟源、都蘭、格爾木、雁石坪、唐古拉山口、那曲、羊八井。克難是因為座位多,臥鋪分上、下兩層,底層又分靠左、靠右及置中的位置。長方形車體,長有七臥鋪,寬有三,再加上下兩層,光臥鋪可賣四十二張票。當然,這還不含走道的床位,以及車後小敞開闊的通鋪。總之,整輛車可裝下七十幾條人乾。多花了錢,買了靠右的上層位,美其名是風景佳,實質是被坑。 從昨夜的凌晨至今,只吃,不說話,像傲慢的獨裁者位居高位。無聊就讀幾本藏地散記,讀累就望窗,撿拾風情,看山河如何壯大,自己又如何渺小。偶爾拿出筆紙,寫些流水帳或詩句,留下隻字片語,像生命的逗點,像潤滑鋸齒。下層的民眾熟得很快,一會兒就稱兄道弟,內地腔,敘鄉土的舊,說大陸各省的變革與鄉野傳奇,有時還拍掌叫好。聽那些話,自知插不上嘴,也就作罷,只管聽。我想他們看我,想必也覺得怪,有人說城裡讀書的年輕人都這模樣,不愛說話。我不僅是城裡來的,還是從台灣搭著鐵翅過海而來。 搭車前,賣票大哥探出我的國籍,票價自然貴些,只怪自己多嘴。那問題還在腦海許久,肚子圓腫的維族司機大喇喇對天地喊:「不載不載,不是中國人我不載。」那氣勢很傲骨。賣票的大哥回得巧:「台灣人哪裡不是中國人?不是都說中文嗎?不都是黃皮膚嗎?你說,這台灣哪裡不中國了?」維族司機被問得窘,有些不知該如何回應,索性開了車廂,叫我自行塞上行李。對話一揚,四周疑惑的眼光聚攏而來,讓我火熱一張臉。我沒說先祖來自福建,我搞不懂為什麼當地人如此在意本國、外國的差異。沒想到,在內陸,當台灣人不容易。 「你說,這台灣哪裡不中國了?」寫在筆記,卻覺得好笑。暫且撇開歷史留下的難題,任何的主張與標籤都可能帶有危險,我笑了笑,原來旅行也那麼容易泛政治化,想要純粹當個浪子沒那麼容易。台灣人入藏需入藏紙,大陸人不用,外國人士卻要。我沒有辦入藏紙,是自助旅行般的偷渡,但非難民。 屁股坐累就換邊,肚子餓就啃些甘甜的桃。想抄下某段音樂歌詞,一遍一遍耐心傾聽當地傳唱的抒情民謠,然而心思總被窗外無所局限的大地吸引,遼闊,高嶺,浮雲與追逐沉默意義的遊子。啊,存在。有水處碧草相連,無水處黃沙紛飛,溪谷小丘,都如此強悍,擁有自我的規律。我赫然發現領略再三的風景,語言的描繪都顯得徒費,我只能呼吸,嘗試成為其中一員。 下午,至格爾木市。司機趕下所有人,說要換車。乘客如群蜂歸巢,緊塞車體左右兩側,各尋行李,挨擠打鬧如辦桌過年。我不喜歡跟人擠,揹了行李就走遠,信步走去。路邊布滿行動攤販,賣氧氣罩、紅景天與葡萄糖注射劑,防高原反應。塞了行李,上車,依票尋位,上面竟坐了老人。我有禮地解釋這個位置是我的,拿出票根當證明,他當沒聽見,不搭理,癟著臉頭撇向一旁。後面的人擠進,我前後不得又發不得脾氣,轉身往底側擠,選了靠右窗的下層臥鋪。問這位子有沒有人坐?無人回應,索性就放膽佔了。我氣自己不敢跟老人吵,又慶幸沒跟老人計較,如果各自都有位置,坐哪裡也就顯得無所謂。後面的乘客陸續上車,各自尋位,根本不在意票根上的號碼與標誌的位置。 許多人不去拉薩,走道空了,未滿。笨重的巴士在格爾木的廣場不斷圈繞,猛撳喇叭,提醒未購票者加緊腳步,下一班車可要等上六小時。半小時後,車停止旋繞,停在廣場,買票者一窩蜂趕市集般上車,有位子就坐,沒位子就擠,距離瞬間挨近了。行動攤販對著窗口兜售藥品,車內幾位大江南北的漢子叮嚀沒去過西藏、沒登過高原的人要買,買了安心,買了有保險,說唐古拉山口前陣子剛有人缺氧而死。我仗著體力好,年輕,平常固定運動,想省鈔票。 位子洗牌後,大陸各省分的人又開始認親,說自己打哪兒來,去過哪些地方,現在準備朝哪兒發展。左側走道是一位三十出頭的瘦漢,用灰色布巾裹住所有行囊。前面擠了位十二、三歲男孩,三分頭,混著維族血統,咖啡眼,發紅發黑的雙頰。置中的臥鋪是穿公安服的壯漢,緊鄰一群工人。後側是位絳紅衣喇嘛,光頭,不多話,沉於冥思。男孩說他七歲就出新疆,在省與省間晃了好幾年,走到哪裡就到哪裡打工,過日子。一旁的人問家人呢?他說他爹也出來晃了好幾年,也沒寄錢回家。娘呢?死了。男孩說得理直氣壯,一點都不畏縮。大夥兒不接話,過了許久才冒出一句可憐。男孩說,這樣的生活才快活。 不久,車上又熱鬧起來,各自罵咧各自言談。有人抱怨,說賣票的最不老實,說好不換車還是換了車,說好不加價還是加了價。有人說鐵路開通後,藏人就辛苦,說他往返多次,發現西藏都變了樣,全都是外地人。還有人說鄉裡工作難找,倒不如去拉薩闖一闖,說青藏鐵路建好後,發展可好,或許可以找到機會發跡。我開窗吹風,沒說台灣、沒說福建,也沒人搭理我這位陌生人。我只是聆聽,南北調,東西情,生活的甕子突然見了天日,好一個浮世繪淺描。 位置過擠。早先在上鋪不覺,如今至下鋪才知臭,開窗都消不了味。味道可濃可烈,菸味、破襪味、尿臊味、身體腥臊味、悶出熱汗的腳味、不知多少人睡過的破毯味,眾多味道叢生雜遝,陣仗使人窒息,我想這也算是另類的民族大融合。人人緊挨,彼此的呼吸、喘息與動作都有了關連,就連口水,也吃下不少。管他大嘴小嘴,歙張吐沫,少不了吞上幾滴他人唾沫。更別說有人打了噴嚏,那水氣甚至比窗外的溼氣大,直往臉上噴。遂替自己念咒加持:入鮑魚之肆,久而不聞其臭。我先是略略厭惡,後是無可奈何,花了冤枉錢,再來又從中得到某種中國式的樂趣─熱熱鬧鬧無所分界。大夥兒倒是一點都不在意,彷彿這種窩擠才有溫度、才夠取暖、才算得上親。 路上,司機又趕人下車解手,大家各司其位,拉開拉鍊,撒下一彎細細水柱。天色好,我拿相機多繞幾步拍照,踅回車時,卻見車門堵出人牆,女子上車,男的不給上,叫我們搭別的車。心一慌,衝進人群也搶著要上車。司機大吼別急,說是先搭另輛車,過了檢查哨再次會合。我怕跟不上車,行囊證件又塞在臥鋪,直說包在車上,怕被偷。不知說了幾遍,司機才許上車。 復回到鮑魚之肆,聞到濃烈的味兒,竟安心起來。天大地大,有啥好怕?就怕半路錢財納賊,病痛猛發。 中國內陸這幾年的秩序比之前好,雖然上車前才被麵攤老闆警告,說我背後有小偷伺機跟隨,準備行竊。攔車打劫是少了,至少沒遇上。病痛卻防不勝防,一注又一注無法遏止的鼻血左右夾攻。我只得猛塞衛生紙,哪邊流就塞哪邊,用嘴呼吸,鼻腔內側都紅腫起來。紙團染紅像喇嘛衣裳,看了心慌。紙團吸飽血,索性拿下,讓鼻孔通風,沒想到隨著長途車顛又晃出兩撇鮮血,紙團又塞,索性仰頭不動。 悲風掠地,白雪掩峰,原可抵上萬貫,抵上千萬詩句,但是看在失血者的眼中,卻了無生意,擔憂來得如此煞風景。下午兩點,車子停擺,司機宣布用餐。我殿後下車,鼻子塞滿血團。同行的另位司機見著,大聲嚷:「別壞了我的毯子,髒了可要賠錢。」我一時氣憤,回嘴:「沒弄髒你的毯。」真是令人難以招架的服務態度。 崑崙山區,近聖山,靠聖湖。腳踏高原應該激動風光,我卻一點都提不起勁,想著身體到底起了什麼反應。司機進屋,幾位湊熱鬧者陸續跟上,叫碗熱騰騰的藏麵。大部分的人,三三兩兩在外蹓躂,吃自備的食物,餅乾、大餅、饅頭、飯糰或是各式甜果。我靠牆啃桃,又嚼了些餅乾,配水喝。同車一位漢子看我直流鼻血,就說這兒高度高,空氣乾,鼻腔缺水,拿些水沾就不流了。我道了謝,感謝他的提醒。上車前,司機又要我們身體減些水如廁。 一路失血,心中非常不痛快。我怪自己不搭飛機,不搭鐵路,現在的折騰活該我受。沾水拭鼻,姑且聽之。車如笨牛緩慢前行,大山大川都已無感,迷倦睡去。醒來是因窗子大開,冷風猛打額頭,一股又一股刺寒。我沒問是誰開了窗,大概車內悶,有人想通風。把窗關小,又睡,醒來又是襲面厲風,索性不睡。 窗隨震動的車體而開,這才發現沒人開窗,是窗關不緊。我的右手撐著窗,空隙一大就往回推。就這樣,一邊吹著寒風一邊推窗也能迷糊睡上三、四個小時。表上七點,天亮得猖狂,且清亮。車子四處響起扯弄塑膠袋聲、咀嚼聲與呢喃詢問時間聲,大家醒來,正各自覓食。維族孩子吃著餅乾,大人分他一些乾硬的大餅與運動飲料。左側的瘦漢拿果凍條狀的肉類製品,看出我的狐疑,分了一條給我,說這是香腸,內地很普通。 「打哪兒來的?不是內陸人吧。」「台灣人。」我坦蕩地說。我將桃子、牛乳和餅乾分給瘦漢以及維族孩子,他們吃得愉快,也拿了一些花生回請。我恍然發現鼻血不流了。沾水,果真有用,不是吹噓空談。孩子問我來西藏做什麼?我答不上話,旅行或者自我放逐對他而言,應該是一種奢侈的概念,一種不存在的空間,一種經濟階級的特權。我說走走,看看。他說他也喜歡走走,看看,不過不喜歡當乞丐,也不喜歡沒有飯吃。瘦漢也問我台灣,說台灣人都是大陸人遷過去的,理應是中國人,為什麼台灣打死不承認呢?我沒跟他討論種族問題,只是笑笑,要他以後有空到台灣走走,看看。後座的喇嘛忽然起了興致,笑著說台灣和西藏一樣,都是流亡政府,都無主權。我也沒和他討論十四世達賴喇嘛的流亡政府,只是笑笑。這些人比我想像中還要可愛,對著世界有各自的詮釋。又是一整天顛簸的行程。比想像中漫長,且疲乏,我總是在這種混沌時刻懷疑起旅行。 夜半,行經高點唐古拉山口,頭痛欲裂,彷彿血管爆了,高度五千二,果真嚴重缺氧。有人拿氧氣罩猛吸,有人咳嗽,有人喘氣,我下意識打開一包餅乾啃,想轉移頭痛。左側瘦漢突然猛拍毯被,無神地左右震盪頭顱,一看,他的身體正不由自主強烈抽搐,口吐白沫,瞳孔上吊,雙腿僵直如失了魂魄。我趕緊大喊出聲,眾人驚醒,慌成一團問發生什麼事。有人說壓他人中,有人說拿東西給他咬,有人說快拿氧氣罩來。慌亂中,備用的氧氣筒與氧氣罩傳遞過來。我罩住他的嘴讓他吸氧,公安漢子溫柔地跟他說放輕鬆,沒事,沒什麼大礙。維族孩子握住他的手,像親人,用衣袖抹去他額頭的髒汙與汗水,跟他說,叔叔,撐著點。司機加快速度,人命要緊,為平緩高原反應從高點往下迂迴疾駛。 瘦漢清醒時,身子還是相當虛弱,講話也有些結巴,此時車近羊八井,高度已降大半。他搔著頭說給人添麻煩,真不好意思,一直向眾人低頭道謝。大家說別在意,都是同鄉,別客套。有人遞出大餅。有人遞出熱水瓶,倒人參茶,要他多喝點。我則遞出桃子給他吃。我的心沉澱了下來,不再驚慌。路途繼續搖搖晃晃,漫遊的空虛逐漸被填滿,我知道,能夠暫時陪伴彼此其實是幸運且幸福的。 「…崇山峻嶺中追趕著太陽,一頂帳篷,一屋情意,從心中讚美春天,啊故鄉,你有那黎明前的蓬勃。你有那黃昏的香甜,啊。」車內的夥伴低聲哼歌,不張揚,不拍掌,彼此卻擁有生動的默契。很不現代的歌,節奏簡單,帶著民歌般的質樸與過於洋溢的熱情,聽著聽著竟也能跟著哼唱。或許,不管遭遇什麼生活,處在何種失離,或疲困或艱難,都必須要有這種高聲歌唱的勇氣,聆聽與吟誦的當下便能更加確立什麼。 眾人的歌聲暫時歇止,目的地不自覺到了,我不捨地告別車上的眾多同鄉。他們把我當成夥伴,看我拿著相機,熟稔地搭摟我的肩,硬是要合照幾張才准我走。回復活力的瘦漢甚至在我的本子寫下他的地址,要我寄些照片給他。他要大夥兒下次一定要到他的故鄉,他會殺雞、請酒、烤肥豬,熱熱鬧鬧辦筵席。我笑了,揹起行囊,步伐邁得更開更闊。入了藏,才發現前方的光比我想像中還要明亮,我必須謹待行旅中每一張臉孔、每一件容易錯過的事物、每一種流逝的人情,這其中一定有著什麼等待我去護衛與敬畏。 |
|
|
送花文章: 5560,

|
|
有 2 位會員向 wulihua 送花:
|